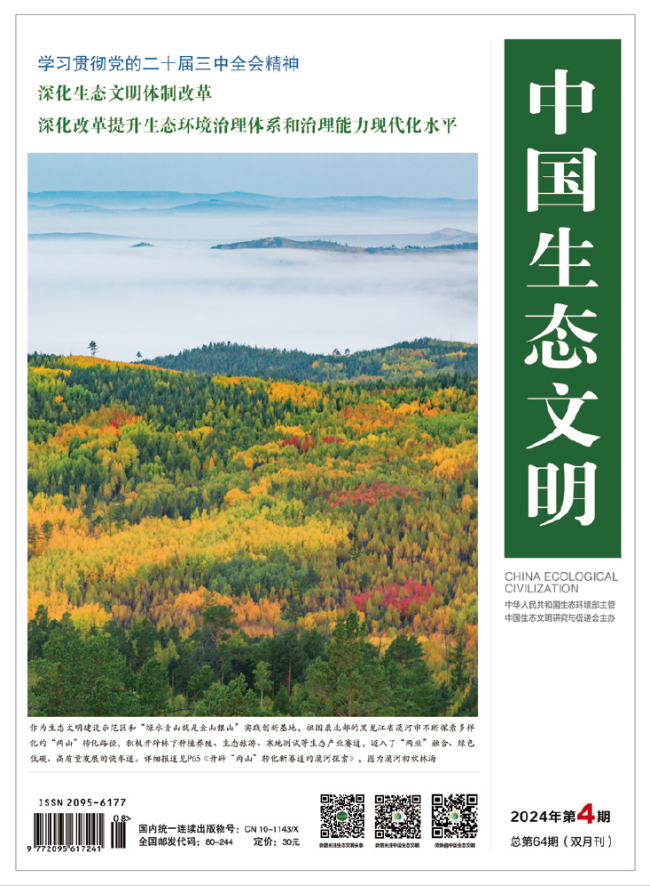天人共美:一種生態的理念
發表時間:2018-04-19
來源:文匯報
作者:楊國榮
隨著歷史的發展,生態逐漸成為人們不能不加以正視的問題。從實質的層面看,生態之所以成為問題,與人自身的存在相關聯。如所周知,人既源于自然并內在于自然,又走出自然并與自然相對,中國哲學中的天人之辯,就涉及以上關系。洪荒之世、本然世界,并沒有生態的問題。只有當人從自然中分化出來(天人相分)、成為與自然相對的另一種存在(所謂自然的“他者”)時,生態的問題才會發生。在人類出現以前,自然誠然也經歷了各種變化,如地震、洪水、海嘯、火山、干旱,等等。不過,這些自然的演化在人類誕生之前,并不構成生態問題。然而,在人作為“他者”從自然中分化出來后,不僅人自身的活動結果逐漸造成了各種生態問題,而且本來沒有生態意義的自然演化也逐漸獲得了生態的意義。如前述的地震、火山、洪水、干旱等變遷,便隨著人類的出現和發展而逐漸地由單純的自然現象,變為生態演化的重要方面,其所以如此,主要在于這些變化直接影響著人自身的生存。從以上方面看,生態的問題確乎與人的存在難以分離:可以說,生態問題首先是人的問題。
生態問題之源于人的存在,與人自身的存在特點相關聯。如所周知,在現實的世界中,只有人才真正具有價值創造的意識和價值創造的能力,也只有人,能夠通過自己的創造性活動而在自然之上打上各種印記。事實上,人生活于其間的現實世界,已不同于本然的存在,而是形成于人自身的創造活動,儒家所說的“贊天地之化育”、“制天命而用之”,便已肯定人參與了現實世界的生成過程。
人的價值創造過程同時也是意義生成的過程,意義本身則有多方面的內涵:它可以展現為正面或積極的趨向,也可以包含負面或消極的性質。從天人關系的角度看,正面或積極的意義體現于和諧的天人關系,負面或消極的意義則表現為天人之間關系的片面化。事實上,生態的問題歸根到底導源于天人關系的片面化,后者呈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由平衡走向失衡。
天人關系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于人們在追求自身價值目的以及進行價值創造的過程中,忽視了自然本身的法則。價值創造的過程固然關乎人的價值目的,但同時又必須本于現實存在以及內在于其中的法則。如果價值目的的追求和價值形態的創造無視甚至蔑視自然的法則,則天人之間便會形成各種張力并趨向于分離,由此進而導致各種生態問題。人的價值創造過程與生態問題的發生之間的以上關系,同時從一個方面表現了生態的問題與人的存在及其活動之間的相關性。
要而言之,生態問題的發生以人走出自然并與自然相對為其歷史前提。如果用中國哲學的概念來表示,則這一前提便以天人相分為其內容。從天人相分或天人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態問題,具體涉及兩重視域:以人觀之與以物觀之。生態問題的解決、生態關系的合理建構,離不開對以上兩重視域的具體理解。
“以人觀之”的天人之辯
生態之域的視域首先表現為“以人觀之”。寬泛而言,“以人觀之”也就是從人自身的視域出發來理解和評判世界,這種“觀”包含多方面的意義:它不僅涉及狹義上的理性認知,而且關乎價值的關切。理性的認知具體表現為在事實層面上對自然本身、自然與世界關系的把握,價值的關切則以天人之間的價值意義為指向。中國哲學很早已意識到以上方面。孟子曾指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里涉及“親”、“民”、“物”三種不同的對象,對待這些對象又有“親”(以親情相處)、“仁”(以仁愛之心相待)、“愛”(以珍惜、愛護之心相待)三種價值立場、價值態度,后者也屬廣義上的“觀”——對事物在價值層面的考察與把握。不僅對“親”(家庭倫理領域中的成員)、“民”(一般社會成員)要給予價值的關切,而且對廣義上的“物”也應當有一種珍惜、愛護(“愛”)之情,這種情感在實質的層面滲入了價值的內涵。宋明時期,理學家們進一步提出“民胞物與”、“仁者與萬物一體”等觀念。“民胞物與”、“萬物一體”意味著將世界之中一切對象都理解為與人相關的對象,并賦予它們以相應的價值意義,這一看法的內在的要求是對人之外的其他對象給予應有的價值關切,其中也體現了以人觀之的價值內涵。
中國哲學不僅在實質層面涉及對自然等對象的價值關切,而且也提出了如何展開這種價值關切的總體觀念或總體原則。后者可以用《中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來概括,即“萬物并育而不相害”。從對待自然對象的角度看,“萬物并育而不相害”意味著自然中的每一個體、每一對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們可以共同存在,彼此之間并不相互排斥。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這里所確認的是,自然作為與人共存的對象,同樣有其存在的意義。以上主要從天人關系的角度,體現了“萬物并育而不相害”在理解和對待自然方面的價值取向。
引申而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不僅表現為理解自然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原理,而且構成了把握人與人關系的出發點。從本原的層面看,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個體、階層、集團、民族、國家在社會領域中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間,彼此之間應共同存在而非相互排斥。與之相聯系,這些個體、階層、集團、民族、國家在享有、運用自然資源上應該具有平等的權利:按照“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則,不同的個體、階層、集團、民族、國家所擁有的以上權利,都應當得到承認和尊重,而不能僅僅強化人類部分成員的權利,否定、排除其他成員的同等權利。但是,在人類歷史的實際發展過程中,以上原則并沒有真正得到體現,相反,我們所看到的,往往是某些階層、某些集團、某些民族、某些國家在利用、消耗自然資源方面遠遠超過甚至壓倒其他的階層、集團、民族和國家。這里無疑包含了人類社會中的不平衡,這樣的不平衡如果不加抑制,同樣將導致生態的問題:當社會領域的某些成員、集團、民族、國家過度地消耗自然資源時,天人之間的不平衡往往會進一步加劇,正如前一代人對自然的過度占有,將導致后來世代的生態危機一樣。以上事實表明,今天的生態問題,與社會上不平等地運用自然資源有著難以否認的聯系。
可以看到,在天人關系之后,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從一個方面體現了前面所提及的看法,即生態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與之相應,解決生態問題也需要從人的角度加以考察與理解。如前所述,以人觀之的“觀”既涉及以理性的方式理解世界,也包括從價值的視域看待世界。從邏輯上說,如果單純地基于工具層面的理性去理解天人關系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往往會引向過強的功利意識,并進而導致人與人的關系以及天人關系的失衡,“以人觀之”所涉及的以上價值關切對于抑制這種偏向,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當然,如后面將進一步討論的,僅僅停留在以人觀之的視域或過度地強化這一視域,常常容易導向狹隘的人類中心觀念。狹隘的人類中心論主要表現為以人類局部的、當下的利益作為考察和處理天人關系的唯一出發點,由此進而趨向于對自然的片面占有、獲取。以上價值取向的邏輯結果,則是導致各種形式的生態失衡。
“以物觀之”的天人之辯
在生態之域,與“以人觀之”相關的是“以物觀之”。以后者為視域,便不僅僅要從人自身的價值目的去理解和看待世界,而且應基于自然本身的規定和法則去考察自然,便由此把握協調天人關系的現實條件。人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需要食物、水、陽光,等等,在此意義上,人也從屬于廣義的生態之鏈。作為自然的成員,人不能不服從自然的運行法則,人本身的活動、發展過程也應當和自然本身的循環系統相一致。從歷史的發展來看,當早期人類還以采集、狩獵等為生存方式時,人與自然之間便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初意義上的循環關系。所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便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人與廣義自然循環之間的彼此相關:人之“作”與“息”的往復,與作為自然對象的“日出”與“日落”之周而復始的運行,呈現內在的一致性。到了農耕、游牧文明的時代,人與自然生態平衡之間的關系問題開始變得多樣化、復雜化。在工業化之后,人逐漸逸出了廣義上的自然循環系統,并由片面地干預、征服自然而導致了各種生態問題。自然系統是人賴以生存的基本前提,自然的破壞以及由此引發的生態問題,最終威脅到人自身的生存,從這一意義上說,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自身。在同樣的意義上,對人自身存在的維護,應當延伸到對自然本身的保護。從“以人觀之”的角度看,人往往被視為目的,而從維護人自身的存在延伸到維護自然,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相應地視為人是目的的延伸。
從哲學史上看,道家對以上關系已有了比較自覺的意識。道家把自然作為第一原則,提出“道法自然”,要求尊重自然自身的法則。當然,“法自然”并非毫無作為,事實上,道家也肯定人的活動。不過,對道家而言,人的活動的前提是合乎法則。這里包含二個方面,即合目的性與合法則性,道家強調活動的合目的性不能悖離合法則性。與之相關,道家提出“為無為”,“無為”構成了“為”的獨特方式,這種“為”的特點在于以合乎自然法則為活動的基本前提。不難看到,道家對天人關系中“以物觀之”這一方面,給予了相當自覺的關注。
然而,道家作為哲學學派,同時存在將自然理想化的趨向。在道家看來,本然或原初的自然就是最理想的存在形態,人應當致力的,是保持、維護甚至回歸這樣一種存在形態。由此,道家甚至趨向于等觀天人,即把天與人視為具有同等價值意義的存在:道家提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這種觀念便意味著將自然與人完全同等看待。其內在指向,在于消解人與自然之間的差異,由此,人作為具有價值創造意識和價值創造能力的存在這一內在規定,也往往難以得到確認。事實上,一旦人作為價值主體這一存在規定被消解,則生態問題本身也將被消解:它意味著重新回歸到天人未分的洪荒之世,此時固然也有各種自然變化,如前面提到的火山、地震、洪水,等等,但這種變化并不構成生態問題。
這里,也許可以對狹隘的人類中心論和“以人觀之”做一區分。如前所述,狹隘的人類中心論主要導源于對“以人觀之”的過度強化,廣義上的“以人觀之”則表現為聯系人的價值目的以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前一偏向應當避免,但后一視域則無法完全擺脫:以生態問題而言,我們之所以努力建立理想、協調的生態系統,歸根到底仍是為人的生存創造一個更為完美、更為合理的存在背景。正如生態問題的發生與人相聯系一樣,生態問題的解決也無法與人自身的存在相分。如果完全拒斥“以人觀之”,便往往容易導向“自然中心”論。道家等觀天人的立場,固然包含多方面的意蘊,但如果對此不適當地加以強化,似乎也可能將人的視域還原為自然的視域,并由此進而引向“自然中心”論。
人的完美與自然的完美本質上具有統一性
以上,分別考察了“以人觀之”和“以物觀之”兩重視域。從解決生態問題的角度來看,合理的進路在于走向上述兩重視域之間的交融。換言之,“以人觀之”與“以物觀之”之間不應彼此排斥和對立,而應相互統一。就生態哲學而言,以上的視域融合包含多方面的意義。
首先是合目的性與合法則性的統一。合目的性意味著人的活動、人在世界中的價值創造,都是追求價值目的的過程。這是人的存在及其活動的重要特點。人的這種價值目的與理想追求不能放棄:如果完全放棄、否定人對價值目的與理想的追求,就可能導致道家曾表現出來的偏向,其邏輯的結果是重新趨向于天人未分這種本然的存在形態,從而消解生態問題。
另一方面,合目的性的追求不應當背離自然本身的法則。這里至少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理解。一方面,人的價值目的本身既基于人自身的需要、理想,又本于現實的存在,后者包括廣義的自然及其內在法則,這樣,價值目的從其形成之時起,便無法離開自然及其內在法則。另一方面,價值目的之實現,離不開人的實踐活動,在實現價值目的的過程中,人的實踐活動同樣不能無視自然的法則,而是需要處處對其加以尊重和服從。人類的歷史不斷地告訴我們:蔑視自然的法則,必然會受到自然無情的懲罰。
如果說,否定人的價值目的趨向于狹隘的自然中心觀念,那么,疏離自然法則所導向的則是狹隘的人類中心論。以合目的性與合法則性的統一為前提,既應當超越狹隘的“自然中心”觀,也應當揚棄狹隘的“人類中心”論。
從更本原的層面看,“以人觀之”和“以物觀之”這兩重視域的交融同時涉及對天人關系的理解。生態問題的發生以天人相分為前提,與這一前提相聯系,“以人觀之”和“以物觀之”這兩重視域的交融與如何面對天人關系這一問題無法相分。時下對天人關系的理解一般都趨向于強調兩者之間的合一。然而,如果作具體的考察,則“合一”本身也包含不同涵義。“合一”可以是原始的、前文明狀態下的“合一”,在洪荒之世、本然的存在中,一切對象處于“合一”的形態之下,與此相類似,早期人類的存在及其活動(如前面提到的采集、狩獵時代的存在方式),與自然之間也表現出原始意義上的合一關系。如果僅僅停留在這一類原始的“合一”之上,那么,人類的歷史發展便失去了基本的前提,生態問題也將既無從發生,也無需考察和解決。當然,人類的發展不能僅僅以天人相分為指向:天人相分的發生和加劇,是導致各種生態問題的根源。合理的取向應當是在天人相分之后,又不斷地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重建天人之間統一。換言之,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回到最初的那種原始的統一形態,而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斷超越天人的分離和對峙,使二者達到更高層面的統一形態。
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看,生態問題只有通過不斷重建天人之間的統一才能解決,僅僅贊美自然的原初形態,一味謳歌、緬懷天人之間的原始統一,只能得到某種抽象、空泛的滿足,而無法真正解決生態的問題。生態的危機因人而起,也只有通過人自己的合理活動來克服。單純地由于人的作用導致生態困境而拒斥人的活動,無異于因噎廢食。在這里,具有積極意義的取向是通過人自身的作用和努力,不斷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重建天人之間的統一。通過這樣一種重建的過程,一方面,人的價值目的不斷得到實現;另一方面,人又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重新參與到自然的循環系統,形成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發展中經常被提及的循環經濟,也似乎趨向于以上理念。在這里,合目的性的價值追求和重建天人統一意義上的生態循環之間呈現相互統一、并行不悖的關系。從更形而上的層面來看,以上趨向同時又表現為中國哲學所肯定的天道與人道之間的統一;從價值意觀的意義上說,它則展現為人道原則和自然原則之間的統一。人道原則包含“以人觀之”,即肯定人的價值目的與價值追求;自然原則表現為“以物觀之”,即尊重、肯定自然本身的內在法則。歷史層面的天人合一所體現的內在理念,就是天道與人道、自然原則與人道原則的不斷統一,“以人觀之”與“以物觀之”兩重視域統一的實質意義,也體現于此。
如果從更為寬泛的層面去理解、考察天人之間的互動,則以上兩重視域的交融進而涉及倫理視域與審美視域之間的關系。“以人觀之”不僅僅意味著注重人的價值追求,它同時也意味著要求人承擔多方面的價值責任,后者既包括人對自身的責任,也包括人對自然的責任。責任與義務處于同一序列,本質上具有倫理的意義,從而,責任的意識背后,包含著內在的倫理視域。另一方面,在合理的生態重建過程中又處處滲入了審美的視域。道家很早就注意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自然本身就是美的。合理的、和諧的生態關系總是同時呈現審美意義,而被破壞了的生態則常常無法給人以美的感受。今天在地球的某些地區,常常可以看到污濁的河流、寸草不長的荒地、灰沙滾滾的道路、廢氣彌漫的天空,等等,這種生態現象不僅在價值的層面呈現出負面的消極意義,而且從審美的角度看也缺乏任何美感。與上述生態現象相對的明凈的藍天、清澈的河流、綠陰如蓋的道路,等等,同樣不僅具有正面的價值意義,而且給人以賞心悅目的美感:當我們將天更藍、水更清作為生態的理想目標時,其中便同時體現了審美的追求。就以上層面而言,“以人觀之”和“以物觀之”兩重視域的統一,無疑內在地包含審美視域和倫理視域的統一。審美視域以美為對象,倫理視域則關乎善,在此意義上,二者的交融同時又表現為美和善之間的統一,后者在更廣的維度構成了人類所追求的基本價值理想。
就價值目標而言,從天人關系和天人互動的角度討論生態問題,最終指向的是人類社會本身和諧、可持續的發展。在這樣一種發展過程中,一方面,人本身不斷地通過價值創造走向完美,另一方面,人生活于其間的世界也不斷地在更高的層面趨于完美。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便同時包含以上內涵。可以看到,人的完美與自然的完美本質上具有統一性,這種統一可以理解為“天人共美”。從一定意義上說,“天人共美”應該成為我們的生態理念。
核心觀點
生態問題的發生以人走出自然并與自然相對為其歷史前提。如果用中國哲學的概念來表示,則這一前提便以天人相分為其內容。從天人相分或天人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態問題,具體涉及兩重視域:以人觀之與以物觀之。生態問題的解決、生態關系的合理建構,離不開對以上兩重視域的具體理解。